银杏观察
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中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的突破。而每个突破对于正处于相同场景的伙伴来说,都会是很好的支持资源、引领、慰藉与激发行动。2023年,悦享新知与银杏基金会联合推出《启发时刻》系列主题探索,本期管理者专题,致朴基金会联合发起人、执行理事长骆筱红分享了她与团队在行动、实践中磨合的漫长历程。每个人在与组织达成共识的同时,也用自己独特的部分为组织文化带来新的贡献。欢迎扫描文内二维码回看完整版对谈。
以下内容来自致朴基金会联合发起人、执行理事长骆筱红在11月9日启发时刻的分享:我们团队如何一起“活出”价值观。
骆筱红讲述了自己和团队一起酿造组织文化这坛酒的漫长历程,六位发起人对人、对教育、对社会的理解带来的价值观是底料,在行动、实践中与团队的磨合和获得各方反馈的过程中,底料一点一点慢慢发酵,包括不同阶段新成员新成分的加入,酿出了一坛既有共识又“不一样”的酒,并且还在持续发酵。
这次对话,不仅让我们看到组织文化如何从底料中慢慢生长,滋养着团队,让每个人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成长为一个更完整的人,也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在与组织达成共识的同时,用自己的“不一样”为组织文化带来新的贡献。
如果你对此次对话感兴趣,欢迎扫描下图内二维码直接完整回看,也可以阅读下方文字版内容。

骆筱红: 大家好,我是骆筱红,一个七年前进入公益行业的六零后。我是师范毕业,进入公益行业之前做过十八年的职业高中教师、八年的家庭主妇,孩子上大学之后,和阿里巴巴的其他几位创始人朋友(五个家庭)一起发起了致朴公益基金会。
我离开学校回家相夫教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教育、对人有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当时体制内的教育并不是我理想的状态。因此,开始做致朴之后,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去探索一些更好的教育的可能性。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在致朴做了六年的秘书长,在第六年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机构的交接。
虽然现在我不是全职工作状态,但我非常喜欢去做事、去一线感知老师们和孩子们,所以仍然会经常参加一些机构实操方面的项目,也会在理事层面支持致朴的发展。今天特别开心能够和大家来聊聊过去六、七年自己在做的事情,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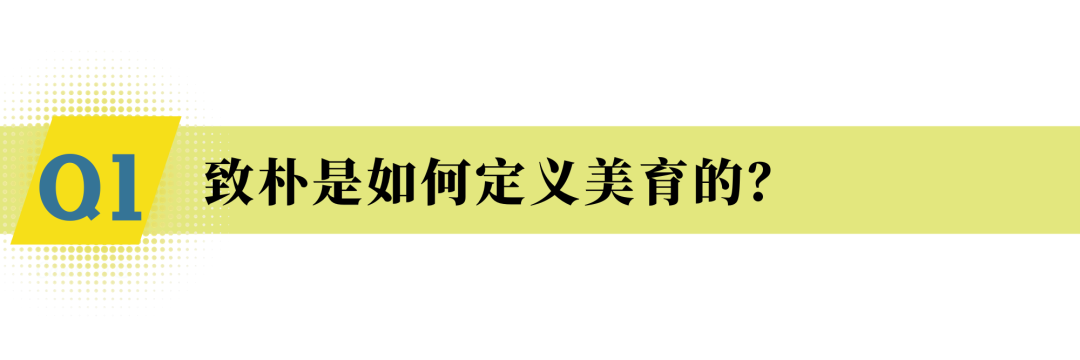
骆筱红:我们并不是去定义美育,而是理解美育。我们认为美育是教育的基础,是孩子成长的土壤中像水一样的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
回到我离开学校的那个阶段,其实我自己是带着很多对教育、对人的困惑出来的。当时已经在喊教育以人为本喊了很多年,但职高的孩子们的状态和外界对他们的印象,都好像他们是“问题孩子”。我知道这些都不是孩子的问题,但是他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为什么他们自己和外界会这样去看待呢?
我带着这些对教育、对人的困惑从体制内的教育出来,到自己想要去做一个机构探索教育的时候,其实还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去回应这些困惑。因为我之前工作的职业高中是杭州美术职业学校,所以创办致朴之后的第一个项目落脚在乡村美术教师的支持。当时我就知道我们不是要做美术,但我们的资源在那里,所以就从美术入手先走着瞧。
直到五年后我们通过理事会战略聚焦在美育。彼时,我们相信美育的价值,但是也仍然心存困惑。比如,我们常常被“什么是美育?什么不是美育?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确认美育是我们认同的教育理念、方法、路径和目标,但怎么说清楚什么是美育依然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新战略确认后,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内部学习和讨论,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困惑的出口:不去定义美育,而是基于我们的实践去理解美育。这是一次思维方式的跨越。
美育最本质的特质是感性教育。一个人需要感性与理性平衡协调发展,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目前我们看到教育的问题,包括以前职高的孩子们和这些年做公益在乡村看到的孩子们,核心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缺失甚至扼杀了他们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与生俱来的感性能力。
美育的核心是回归人与生俱来的感知来认识世界的学习方式,包括感知、直觉、想象、创造,这是一个人完整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美育给教育带来的基本价值。
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孩子是在土壤里生长,美育是这个土壤里像水一样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一直说致朴是一个教育公益机构,不说我们是一个做美育的机构。我们内部已经打通了这个理解,但可能很多伙伴会困惑,觉得是不是你们觉得美育可以代替教育,其实不是的。
美育不等于艺术教育,但是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路径。艺术教育重视人的感觉、直觉、想象、创造,尊重人的主体性和差异性。以体验作为学习的起点。这也是我们认为美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我们从美育的特质里找到教育所共通的底层价值。虽然我们对美育也还在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当中,但我相信,尊重个体感受应当是所有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骆筱红:如果把组织文化比做一坛酒,基于创始人团队对人、对教育、对社会的理解和向往带来的价值观是底料,团队在行动、实践中对底层价值观的解读和生发就像底料一点一点地慢慢发酵,包括不同阶段新成员新成分的加入,持续酿造着组织文化这坛酒。
组织文化的生成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我们坚持做下来了,也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真正去理解了怎么去影响人、怎么去相信人的完整发展。
“最难是知行合一”,确实致朴六、七年这一路走下来,中间有很多的张力、挑战和选择。我特别开心的是我们的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这一路走过来,虽然经历各种困惑和挑战,但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下,在机构里生长。
致朴创立的时候,首先承载了我们几位创始人对人、对教育、对社会的理解。我们几个为什么要做一个公益组织?其实是基于对一个更理想的、更美好的社会向往,希望我们能在其中有所参与。美好的社会是由美好的人构成的,教育是我们认为去支持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美好的人的重要的路径。
发起致朴这个基金会的时候,我已经50岁了,我们机构的发展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我们这些发起人对人、对社会、对自我的认知为起点而开始的,在这个起点里,我们就知道人的重要性。我们期待去做一个“百年小而美”的组织,这是一开始就确立的组织定位。
当时我们几个发起人没有聊太多东西,就三点:第一要做小而美的百年基金会,不要做大;第二要做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第三如果我来操持的话就要做教育,因为别的我不会(笑)。因此,这个“小而美的百年基金会”本身就承载了发起人对组织和对人的期待。
作为机构主理人,机构发展的前几年最大的阻力其实是我个人成长的挑战,这其实也说明了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去做事。在我们成立第一年,就已经确立了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当时我还没有战略的概念,我说我们要做三件事:确立机构的文化基因;建构机构的核心团队;项目的基本方向。当时我就想五、六年后我是要交班的,机构要成为社会化专业运行的组织,而不是几个家庭的私人产品。前三年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组织文化基因构建。
机构成立的时候我们就确立了使命、愿景和四条价值观——儿童本位、乡村优先、协同成长、独立价值,但这四条价值意味着什么,当时是没有解读的,但这些是我们发起人的价值诉求,是我们捐赠的钱附带着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就好像是组织文化里的底料,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慢慢发酵成一坛酒,并且现在还在持续发酵。这些价值观支持着机构的成长,成为一种团队的文化氛围,团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从行动当中、从项目实践需要当中,从价值观一点点地生成了一条一条的组织文化。
举个例子,致朴组织文化中有一条叫“相信激发的力量”。当年我们新来的员工才来了一两个月,就去组织教师培训,看到有个老师在培训场进进出出,基本不再状态。这个伙伴就来问我:骆老师我该怎么办?我要让他在这里吗?我要跟他说你不要来参加了吗?这样的人我该怎么办?我跟她说:我没有答案,你先自己去想。
后来我们过“致朴日”讨论组织文化的时候,她就把这个困惑提出来了。如果简单从项目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老师不让他入项好像就解决了问题,因为他好像没有内在的需要。但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慢慢形成了“相信激发的力量”这个共识,我们底层的相信是每个人都是有可能被激发的,每个人被激发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的员工要去寻找激发那个人的方法。
接着,我们又形成了对这个条款的具体解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在漫长的行动的过程中,我们又一点一点地确认了怎样的激发是有效的、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并没有给到具体的方法,但给出了一些方向、原则和价值,让伙伴去发挥对人的重视,去实现底层相信的知行合一。
这个例子其实是想说明,组织文化的生发的漫长过程,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但又极其鼓舞人心的过程,也是我自己觉得特别开心的过程,我们看到了想要的东西。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面临平衡和选择,比如效率、成果等等。并不是说不要成果,而是在寻找两者平衡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坚持什么东西是这个阶段更重要的。
以“相信激发的力量”为例,确实可能会面临项目效果和组织文化之间的碰撞,你是要去追求一些及时的看得见的效果,还是要去激发这个人,这其实是不同机构的不同选择。比如我发起的另一个做疾病的机构,跟致朴走的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它是从项目入手的,但这两年开始回过头来找文化,所以我觉得底层理念的拉齐其实是绕不过去的。
回到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组织文化的生成过程中感受到自在,我觉得是个体自我与机构文化是不是能匹配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有同事觉得彼此不合适就离开的。我们招人的时候会先初步确认一下彼此的文化价值是不是一致的,在工作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让同事感受到不断地突破和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他应该也会觉得很自在。
我们有条组织文化叫“因信任而简单”,在团队磨合过程中,我觉得是最起作用的。每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都努力创造安全的氛围,鼓励大家把真实的感受说出来,信任就是我可以不怕别人质疑,我可以说出来,这个当然也是要构建的。我特别为致朴的伙伴感到骄傲的,就是他们可以慢慢获得信任和打开,去经历和成长。
组织文化其实是让每个人在组织中自在成长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如我自己,之前我做校长的管理风格,就是自上而下的我说了大家干活,转变成今天这样的一种状态,也是经历了不断的挑战和成长,也特别开心我自己觉得今天的我比十年前的我要好很多,是我自己更喜欢的我,也特别感谢致朴的同事们在这个过程中支持我一起成长。
新的伙伴也一定是组织文化的贡献者,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去接受。我们发起人带来的价值观是底料,新来的同事既可以从底料中吸收自己需要的、有营养的东西,也可以把自己带来的东西贡献出来,去与底料产生化学作用,形成新的文化,让这坛酒越酿越不一样。
组织文化的生成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我们坚持做下来了,也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真正去理解了怎么去影响人、怎么去相信人的完整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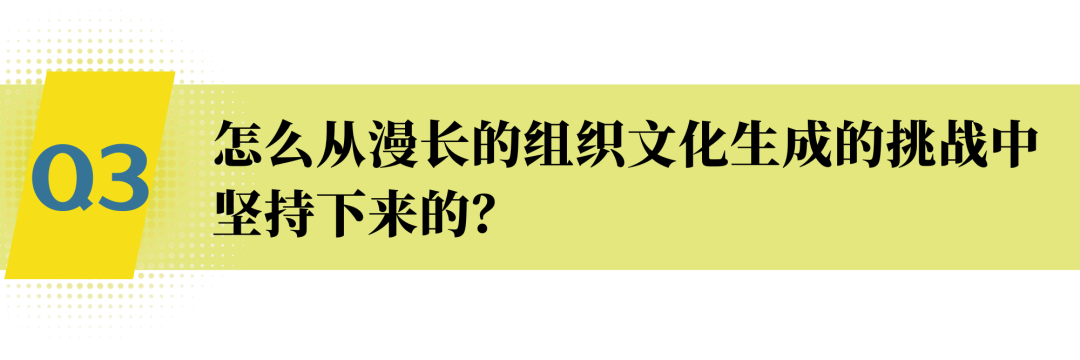
骆筱红:组织文化是指引行动的方向,坚持的过程其实是在实际工作中对文化的确认感和从各方获得积极反馈的过程。
一方面我们几个致朴的发起人在创办机构的时候都已经人到中年,本身有了自己对人的价值的确认感,这种确认感是存在的,创办致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把这种确认感做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收到来自内部和来自伙伴的积极反馈,让我们去确认。
致朴的组织文化是对应着具体的事情和实际的工作的。
比如我们每几个月会有一次“组织文化故事复盘”,是要团队去记录和思考每一条组织文化与工作中的细节是不是相符或相悖的,每个人都要回到行动里面去找组织文化,它并不是一个脱离工作、完全务虚的东西。它在我们自己、我们的合作伙伴、服务对象包括我们的孩子那里,都是能够看到积极反馈的。
当然组织文化也会存在无法形成共识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先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讨论,可能会形成新的共识,也可能存在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情况,这也是存在的挑战。
即使没有在组织文化层面形成共识,行动中该做的决策也还是要做的。组织文化是信任层面的东西,或者说是指导我们工作的一个方向。组织的发展除了文化,还需要有管理的制度机制,制度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产物。
对我自己而言,很难的时候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让我让组织变得更好的。我们发起人、理事会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让我去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化,有没有让我们离教育的本质、人的本质更近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特别不容易的、让我觉得崩溃的时候,让我能够坚持下来的其实也还有美育带给我的积极正向的力量。第一是和我的年龄有关,我经历过的事情、参与过的学习给了我很多的收获;第二是每个人获取能量的路径不同,我是特别能从儿童那里获得能量的人,在致朴的工作让我能够有机会和儿童在一起,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倡导的教育价值,让我感知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获得要把这些事情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当我有了这些动力,那些障碍就不是特别大的障碍了,最重要的是当我突破这些障碍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自己跟原来不一样,变得更松弛更开阔了。当你变得越来越松弛,同事与变得越来越好,团队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让自己更有能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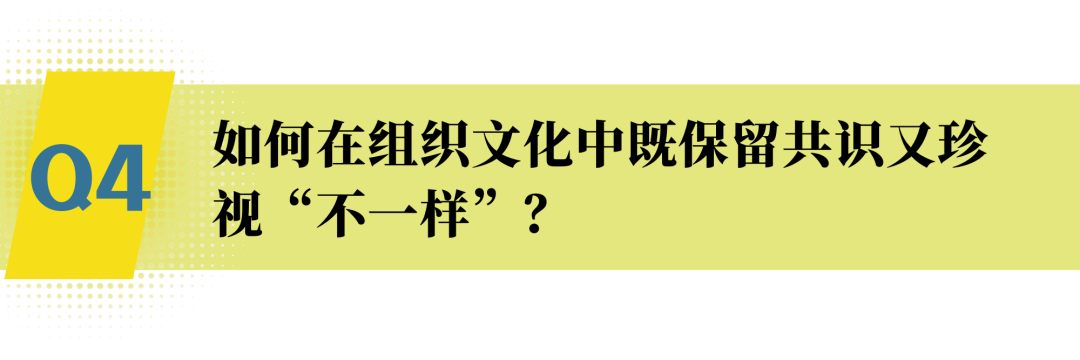
骆筱红: 作为机构来讲,一定会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求、共同的任务去完成。我们会去探讨什么可以一样,什么可以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珍视的“不一样”不是“你说啥都是对的”,而是在于你可以安全表达,充分地展示你的不一样,而不是“藏”起来。
另一方面因为致朴的工作是创造性很强的工作,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创造的机会,你可以用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去感知自己和致朴重叠的一样的部分有多大,要不要继续往前走,我们愿意付出这个磨合过程的代价。
一旦磨合好了这个东西,会让员工爆发出自己非常大的能量,达成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尊重伙伴用符合致朴对美育的理解、对人的理解的他自己的方式,去支持人。
文字整理编辑:李洁
封面设计:大宝
排版:蔡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