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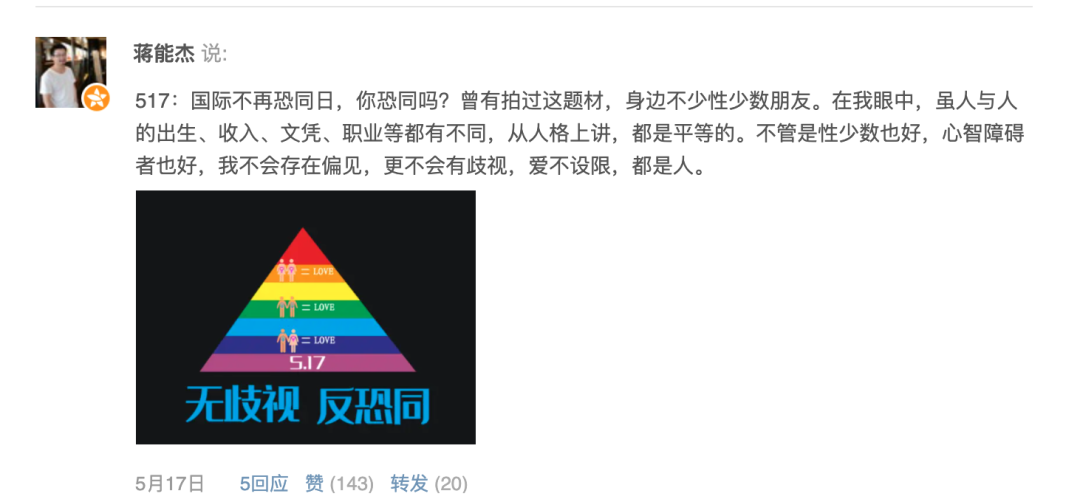
点击播放《彩虹邮轮》预告片
[1]《彩虹邮轮》为银杏基金会2020年支持的银杏伙伴合作基金项目之一,项目共同发起成员有:胡志军(出色伙伴)、蒋能杰(棉花沙影像工作室)、冯璐(北京丰台利智康复中心)。银杏伙伴合作基金(以下简称“合作基金”)由银杏基金会与银杏伙伴共同发起,通过资助项目的方式,鼓励银杏伙伴之间的合作与创新,形成集体影响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2] LGBT一般指性少数群体,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跨性别、间性人等都属于性少数群体 。

挖掘社会创业家成长、行动以及ta们与社群连结那些事儿


